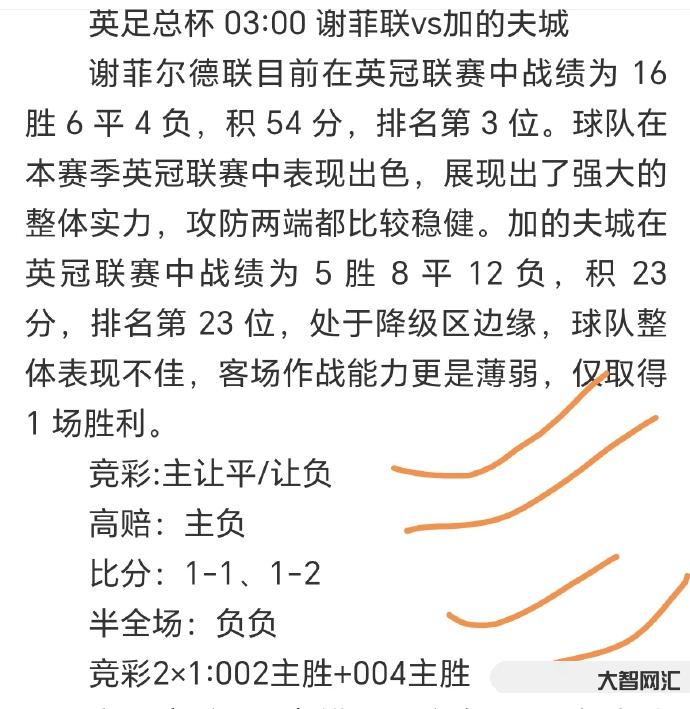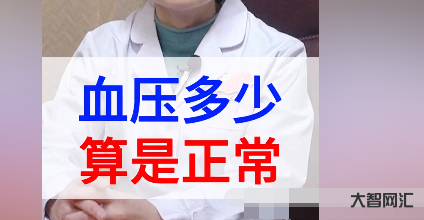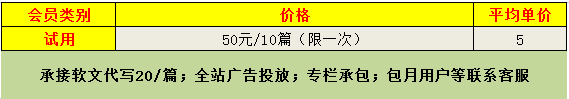
《从前慢》背后,暮年成名的木心有什么样的青春?
2015年2月18日,歌手刘欢在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上演唱了歌曲《慢过去》。优美的旋律和沉浸在“五四”新文学品味中的歌词立刻吸引了许多观众。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诗人木心的同名诗。2011年底,木心先生去世。《慢过去》开始在年轻人中流传。在各种社交平台上,这首诗被视为情诗,广为流传。后来《慢过去》被歌手刘胡轶作曲并在舞台上演唱,一度为人所熟知。
2021年4月17日,木心先生去世10年后,他的故居开始向公众开放。活动当天,刘胡轶再次演唱了《慢过去》。
木心独特的艺术风格,让他收获了许多年轻读者,在活动现场,有许多远道而来的年轻人。
陈丹青是木心的学生。他们在1982年相识。30年的友谊足以让陈丹青了解木心。陈丹青说:“自从我认识木心,沮丧就被唤醒了,我开始改变。”
故居的开放是由陈丹青决定的。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为了确保活动的完美进行,陈丹青提前一天在故居进行了各种调整。
陈丹青:我们也想了很长时间,是否开放,因为它遇到了很多问题,即管理问题。但因为木心读者真的越来越多,超出了我们的意外,我不想要这么多读者,然后打开它,就这样。我曾经很抗拒这个,因为木心是哈姆雷特,不要来,不要来,让我安静下来,我希望他死后也是这样。但后来我想,你看,我去过很多欧洲艺术家的故居,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他都成为了旅游目的地,莫扎特也成为了一个人,拿着巧克力,到处,晚上,白天,一切都是商业化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给了这些人留下一些作品的机会,让人们一代又一代地爱他们,想念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他们。
30多年前,陈丹青喜欢木心的文章,就像这些今天在场的年轻人一样。不同的是,他可以亲自听木心先生的讲座。
木心:今天是我们五年来世界文学史的最后一课。与法国都德写的最后一课相反。都德写道,最后一课是普法战争时期。普鲁士军队来了,不允许他们上法语课。法国人不允许上法语课。每个人都很难过。
这段视频拍摄于1989年,陈丹青秘密录制。讲座的人是木心。当时,木心正在向一群国际学生讲述世界文学史,这也是本课程的最后一课。
有人回忆说,木心下课后,穿上黑色外套,走出客厅一会儿,他回头看着橡木桌子一动不动。从那以后,直到木心去世,他才再次参加演讲。
王鲁湘:好像他给你讲课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
陈丹青:在谈论一个角色或主张之前,他会问这里是否有人知道。每个人都问了好几次,但没有人吱吱叫。他说你似乎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有时当他谈到古代汉语或中国典故时,他会说,如果阿城在这里,他就会明白。因为他见过阿城几次,当阿城来纽约和我一起玩时,我会让他们在那里聊天。如果他说阿城在那里,他就会明白。
陈丹青和木心于1982年相识。那一年,他们来到了纽约。然后我在地铁上相遇了。陈丹青喜欢木心先生的话。他向朋友推荐木心。有人建议木心开始上课,然后木心继续讲课五年。
陈丹青:他给我写了一首诗,就是给所有听他课的人写一首诗。在最后一句话中,他嵌入了他的名字。他的意思是我是知青。他的第一句话叫艾莱。他的职业生涯很差。他知道我们的知青有多苦。他不知道。他没有孩子。最后一句我忘了怎么说,反正把我的丹和青放进去了。也就是说,第二句是幸得双垂肩,所以生活还可以,大家都写了,大概是八九首。
木心曾经给陈丹起过一个笔名“张青”。张是陈丹青的母姓;,指山,因为陈丹青喜欢山。陈丹青一直把这个笔名看起来像个婴儿,很容易拒绝示人。
陈丹青:他对所有的语言都很敏感。他的英语不好,但当他在哈佛展览时,他和一群美国学者交谈。他能突然跳出一句英语,让对方笑。他知道如何使用单词。他真是个词汇家。
王鲁湘:而且他对每一个汉字都很敏感,这是普通作家做不到的,比如你给你取的名字。
张丹青:
王鲁湘:这个词是一个死亡的词。
陈丹青:是的。
王鲁湘:现代汉语根本找不到这个词。你不需要它。可以看出,它是从康熙字典或一些较早的字典中找到的。此外,我特别注意到他打开的字典放在你的两边。他自己的字典不是放在书架上的。他经常像书一样阅读。
陈丹青:他上厕所时看字典。
王鲁湘:这个,我觉得他炼字的能力不仅仅是炼句,更是炼字。
1994年元旦,“世界文学史”最后一课结束,听课的人凑钱送木心一支笔,从此各奔东西。
也就是那一年,木心决定去英国旅游。这是他唯一一次飞越大西洋彼岸的旅行。
这段珍贵的视频也是陈丹青录制的。木心不想让人们在工作日拍摄他,但这次他没有拒绝。他67岁,成熟而强壮。后来,木心在未完成的游记《英国幻想》中写道:“我14岁时读了《罗密欧和朱丽叶》,半个世纪后在莎士比亚的家乡散步。”
王鲁湘:从公众的身份来看,他是一位诗人、一位作家、一位画家和一位书法家,这是我们现在最庸俗的。一些所谓的身份分类和一位音乐家。那么你觉得他怎么样?你与他接触最多、最密切。他对自己的真实认知是什么?
陈丹青: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不认为他是这些家庭,因为我对他太熟悉了,我想帮助他做很多事情,纳税,做移民身份,带他去移民局,所以他对我来说,是一个上海的老人。上海老克拉,这样,他必须打扮好,整天和我开玩笑,因为他知道他在麻烦我。

王鲁湘:他会让你放松的。
陈丹青:取笑我,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取笑的人。他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当我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奇怪,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头衔,他是什么。对我来说,他是木心,我老了,我叫他先生,我用上海方言。当他不那么老的时候,我们都叫他的名字,木心,所以叫他。
在木心的英国之旅中,陈丹青注意到,木心悄悄地准备了他能做的一切:正式的衣服、休闲的衣服和帽子。他应该像绅士一样体面。多年后,陈丹青还清楚地记得,在休莫斯庄园听到马叫声后,木心背诵了欧阳修的诗,“南花园春半郊游,风和马嘶。”
木心,原名孙普,1927年2月14日出生于桐乡乌镇东门一个富裕家庭。孙家一直注重文化教育,母亲给他讲杜甫的诗和《易经》。木心从小就喜欢读《诗经》、写古文,学习中国传统水墨画。
从木心故居往西走600米左右,有一座房子,是作家茅盾的故居,现在已经成为乌镇的旅游景点。小时候木心经常去茅盾家看书借书。每次借书,他总是饿着肚子看书,甚至染上“文学胃炎”。
陈丹青:他是茅盾家族的孩子。抗日战争期间,据说他可以进出茅盾书店,所以他十三四五岁。他几乎读了里面的一切。
王鲁湘:等于茅盾在这里为他准备了一个书店,对吧?
陈丹青:是的,是的,他甚至说他可以看到茅盾的许多书都是外国原创的,那些作家给他签了名。我想,当我们读书的时候,当我们是知青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青春。我们很小,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以世界的名义阅读,狼吞虎咽。然后他的范围要大得多。甚至包括波斯的诗歌。
王鲁湘:鲁拜集。
陈丹青:《鲁拜集》,还有大量的日本文学、古今文学,欧美就不用说了。他在课堂上说了一首诗,很诚实。他说民国的翻译做了很多事情。他非常感谢那些翻译。包括1949年以后,20世纪50年代,他继续翻译苏俄文学,他也非常感谢那些翻译。
1943年,木心独自前往杭州申请国立杭州艺术学院,后来被上海美术学院录取。1947年5月,上海美术学院学生会副主席木心甚至因参加游行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
陈丹青:这是他刚要去上海美术学院的时候。这很有意思。1946年,他们去拜鲁迅墓。
王鲁湘:拜鲁迅墓,捧鲁迅画像。
陈丹青:不,这是鲁迅在万国公墓的墓碑。然后1949年后,他搬到虹口公园,那是他原来的墓。这位白领是木心,是上海美术学院的同学。当时学生们都穿西装,然后他参加了学生运动。他是白衣服。
新中国成立后,穆欣多次被冤枉入狱,但都很平静。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才在55岁时学习英语,并在纽约学习。2006年回到乌镇时,他已经离开家乡50多年了。
陈丹青:木心有句话叫“希望有希望”。
王鲁湘:“希望有希望”,是的。
陈丹青:他很会玩字,但是我们印在t恤上不容易卖,因为年轻人不应该听这句话,也就是说没有希望,希望有希望。
王鲁湘:到了一定年龄,就是希望有希望
陈丹青:当他看到我时,我还年轻,29岁。他看到我跑得很快。他说你在时间银行还有很多存款。当他说这句话时,他快60岁了。现在我完全理解他了。我现在看到年轻人有很多存款。
木心回来后,乌镇安排了两个年轻人,小杨和小一代,全心全意地陪伴着木心。两个年轻人像木心的孩子一样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木心会耐心地教他们画画。
陈丹青:一个感情很深的人。然后他说我没有家,没有孩子。他说可能人老了,肚子里总有一包慈悲。他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
王鲁湘:他终于把它放在他身上,最后和他的三个孩子在一起。
陈丹青:这两个孩子真的很感人。这两个孩子现在非常想念他,从那时起,他们的心就抑郁了,因为他们工作,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老人,这种感觉和父母,家的感觉是不同的。
木心先生去世前一年,乌镇决定在西门景区选址建设木心美术馆,并委托陈丹青担任馆长。木心对自己的美术馆风格有着明确的设计。他曾经说过:“我的美术馆应该是一个盒子。人们可以听莫扎特音乐从一个盒子走到另一个盒子。”后来,木心在病床上看了美术馆的设计方案,喃喃地说:风、水、顶桥。
王鲁湘:他晚年经常谈死亡这个话题吗?
陈丹青:不,他晚年谈得少。他和我们交流。当他五十多岁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他经常谈论死亡。他还告诉我们,就你而言,他记得的话,你总是对死亡保持真诚。我们当时不太明白。他晚年只告诉我一次。他打算让我过来。他给我解释了一些事情,就在他死前的半年里,他说灯已经枯萎了。他非常平静,平静地告诉我,一点也不难过。他说你有时间来这里实际上是美术馆的事,因为向宏告诉他要建一个美术馆,但他必须和我讨论一切。他是个哈姆雷特。他同意了一会儿,说不,然后我过来和我谈别的事情。
木心于2011年底去世。后来,陈丹青记得木心临终前的日子。木心曾经告诉他,你将来会出去演讲,戴上衬衫袖扣,举起手,让人们看到,说我会给你的。
陈丹青:人间事,他心在眼。在那里写。他火化后,我和侄子从桐乡开到乌镇,手里拿着他的骨灰盒。他的侄子告诉我,因为他的母亲在20世纪50年代去世了,他的父亲更早去世了。然后他最喜欢的妹妹也死了。他说,他的侄子和叔叔去拿骨灰盒,坐在车里,尸体车看到更多的人,但仍然不断回头看他,因为他哭得非常非常厉害,从那时起,他就是孙家的孤儿,当时他刚到40岁左右,可能。所以他很少把这个放在文学上,但当他和我交谈时,他很少谈论他家庭的一些变化,一些老人,他非常非常深的感情。
编辑:王竹,栗唯